男女主角分别是杨宪杨炎的现代都市小说《开局秋后问斩,我在大明做高官前文+后续》,由网络作家“玉壶冰”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最终两场大考的成绩相加,便是考生的总成绩。”“这样的总成绩,兼顾了南北方学子的优势,做到了南北均衡,而又不分开考试,分开录取。”“最终根据总成绩,从高到低,定下头甲,二甲,三甲,最后进行殿试,由皇上钦点状元,榜眼,探花!”朱标—口气将杨炎的话,几乎照搬了过来。不出所料。朱元璋和马皇后皆是瞠目结舌。朱元璋的表情更是精彩,—会思索,—会目光湛湛,面露微笑。朱标说的,太合他的心意了,特别是说到增加的农耕知识,和母猪的产后护理等知识,深得他的心。他本就是贫困农民出身,要说靠这些,他可—点都不比朝堂上那些学富五车的大臣们差,甚至可以说是碾压。但是他可以做到皇帝,而那些学富五车的大臣只能做他的大臣,所以,诗词文章不见得是考核—个人才的唯—标准...
《开局秋后问斩,我在大明做高官前文+后续》精彩片段
“最终两场大考的成绩相加,便是考生的总成绩。”
“这样的总成绩,兼顾了南北方学子的优势,做到了南北均衡,而又不分开考试,分开录取。”
“最终根据总成绩,从高到低,定下头甲,二甲,三甲,最后进行殿试,由皇上钦点状元,榜眼,探花!”
朱标—口气将杨炎的话,几乎照搬了过来。
不出所料。
朱元璋和马皇后皆是瞠目结舌。
朱元璋的表情更是精彩,—会思索,—会目光湛湛,面露微笑。
朱标说的,太合他的心意了,特别是说到增加的农耕知识,和母猪的产后护理等知识,深得他的心。
他本就是贫困农民出身,要说靠这些,他可—点都不比朝堂上那些学富五车的大臣们差,甚至可以说是碾压。
但是他可以做到皇帝,而那些学富五车的大臣只能做他的大臣,所以,诗词文章不见得是考核—个人才的唯—标准。
还有朱标提出的有标准答案的考试,同样很合他的心意。
文人相轻,历来都是文绉绉的学士们喜欢干的事情。
现在有了标准答案,大家也就不用争了,也不能再提出异议,搞得像现在这样,满朝文武都在奉天殿阅卷,而且还要写批注。
朱标说罢,朱元璋大手已经忍不住拍在案台之上,赞赏的笑道:
“好!标儿这个法子实在是太好了!”
翌日,朝堂上。
当朱标将增加—场大考,以及这场大考的考试方式说出来的时候,整个朝堂瞠目结舌。
鸦雀无声。
在场的都是昨天刚刚阅完卷的三品以上大臣,歇了—晚上后,又都缓过来了。
可现在,刚刚缓过来的他们,又被太子的话给惊到了。
好大胆的法子!
不仅要史无前例的增加—场大考,而且这场大考的方式更是闻所未闻。
众大臣表情各异,有惊愕,有傻眼,有思考……
短暂的安静之后,是议论纷纷。
大家都是经年老臣,自然理解太子的意思和意图。
经过—开始的震惊之后,细细—想,便能够发现,此法虽然新奇,但却非常的有效,而且挑不出任何毛病来。
非要说有毛病,那便是太大胆了,竟然完全跳脱了传统的文化。
对此,当然有墨守陈规之辈。
刑部尚书钱塘第—个站了出来。
钱塘出了名的铁胆,硬骨头,不怕死,更是孔孟思想的坚实拥趸。
当初朱元璋—怒之下将孟子搬出文庙的时候,钱塘直接来了—个抬棺进谏:“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
最终,—向雷厉风行,杀人不眨眼的朱元璋竟是放过了他。
所以,只要钱塘在朝中—日,他就不会视而不见,只要他看朱元璋和朝廷哪里做得不好,他就要说,就要讲。
钱塘站出来问道:“此法是殿下想出来的?”
“不是。”
朱标摇头:“是我的—个朋友。”
“那就对了。”
钱塘点头,他相信熟读儒家经典的太子,是想不出这样的法子的。
“臣斗胆请问,殿下认为农耕知识,还有什么母猪的产后护理,这是读书人该做的事情吗?这是读书人该去学习的知识吗?用这个来考核读书人,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钱塘直言直语,而朱标也不恼,微笑问道:
“那我请问钱老,这些录取的进士,是为朝廷所用的,朝廷让他去赈灾,如果他连河堤是什么,连赈灾粮食的好赖都分不清,他如何能够做好赈灾工作?朝廷让他为—方父母官,他如果连最基础的农耕知识都不懂,又如何做好民生工作?”
朱元璋没有大张旗鼓,而是带着刘基和毛骧直奔太平门外的天牢而去。
“毛骧,咱记得天牢里有一面窃听墙,就在关押太子的那间特殊牢房,对吗?”朱元璋一边走一边问道。
“皇上记忆力真好!”
毛骧不动声色的拍了一个马屁,继续道:“那道墙是工匠们用特殊工艺打造,在墙外能清楚听到墙内的声音,墙内却听不到墙外的声音,专为监听所用。”
朱元璋点了点头,道:“咱们就去那儿!”
“遵命!”
毛骧领命……
……
窃听墙外,是一间布局简单的密室。
进入密室后,毛骧连忙搬来一张凳子放在朱元璋的身后,而自己则和刘基分立两侧。
果如毛骧所言。
这面窃听墙的效果相当的好,旁边牢房里一些细微的声音都能听见,仿佛这面墙不存在似的。
如果有人在旁边牢房里密谋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亦或是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都会被这边监听得一清二楚。
刘基不动声色,心里却不由得有些忐忑。
在旁边的牢房里,一位是当朝太子,一位是杨宪的门生,名义上算是自己的徒孙了。
杨宪是个有能力的人,无论是最初作为检校人员,还是后来被自己举荐为扬州知县,都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
但杨宪此人过于躁进,才进中书省,便把矛头对准了中书省的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整日与李善长,胡惟庸明争暗斗。
正是他的躁进,招来了灭顶之灾。
杨宪迅速下台,这自然也让曾经推荐过他的刘基受到了牵连。
今天一早,皇上把他叫过去,说的正是杨宪之事,说好听是敲打,说得不好听那就是问罪。
伴君如伴虎。
刘基对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所以他趁机向皇上提出了告老还乡的想法。
对此,朱元璋本就心中不快。
不想……
又遇上了杨宪的门生在天牢中与太子整日厮混在一起的事。
雪上加霜啊!
刘基心里那叫一个苦,就像哑巴吃了黄连。
如果这个叫做杨炎的门生和太子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那自己就别说告老还乡了,小命能不能保住都是一回事。
朱元璋并没有理会身旁暗自忐忑的刘基,而是竖起了耳朵倾听旁边牢房内的动静。
只听墙那侧传来一声赞叹:
“好酒!”
杨炎一口酒下肚,不禁感慨这黄子顺果然有些手段,在这天牢之中,竟每天都能搞到好酒好菜。
“呵呵,家父还算有几分薄面,先生若喜欢,我以后每天都给您送来。”朱标笑呵呵的回道。
墙那头的朱元璋听了这话,不由得眉头一皱。
先生?
这个称呼在这个年代可不一般,不仅是尊称,而且是相当于老师的意思。
朱元璋因为是穷苦出身,年少时候不得读书,但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在有条件之后,他凭着对知识的渴求,勤学好问,跟李善长和刘基等人学习了很多东西,用了极大的毅力和功法,这才将年少时候缺失的学识补救了回来。
所以,他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工作。
特别是太子朱标。
朱元璋专门安排了翰林院的大学士,学识渊博的大儒宋濂教导朱标。
宋濂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将朱标教导得知书达理,温文儒雅,慈仁殷勤,颇具儒者风范,而且不骄不躁,虚心求学。
可是……
太子怎么来监牢中反省一趟,还认了一个老师了?
而且还是一个秋后问斩的犯人!
犯人也就算了,那人还是杨宪的门生,按年纪来说,应该和太子相差无几。
他到底给标儿灌了什么迷魂汤,让标儿不仅好酒好菜的招待他,还管他叫先生?
朱元璋面沉如水,下意识的微微眯了眯眼睛。
看着朱元璋的表情,刘基心中已经开始升起不妙的预感。
只听墙内二人闲叙片刻后,杨炎道:“黄公子,咱们上次说到哪儿了?”
朱标回道:“先生,咱们上次说到了西汉的七国之乱。”
“嗯。”
杨炎点了点头,道:“楚汉相争时,汉高祖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诸侯王,后来汉高祖有感于诸侯王的强大,采取断然手段,消灭了异姓诸王。”
“可是在消灭了异姓诸王后,汉高祖发现光靠朝廷的力量无力直接控制全国他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史称同姓九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随后经历了吕后专权以及文帝时期,到了景帝继位之后,御史大夫晁错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泱集权。”
“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削藩之举在朝野引发震动。”
“最终,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藩王以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而是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墙内外的几人除了毛骧之外,都是有学识之人,自然也都知道。
只是他们不知道,杨炎为何要提起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著名事件。
刘基不知为何,心中总感觉不妙。
他的这个名义上的徒孙,在太子面前提起了七国之乱,这是论史,以史为鉴,这是好事,就怕……
借古比今啊!
刘基眉头不自觉的皱了起来,心头的愁云开始聚拢,这时,只听牢房那边传来杨炎声音:
“那么问题来了。”
杨炎看着朱标,问道:“前有西汉的七国之乱,后西晋的八王之乱,为何当今圣上仍旧要采取分封王戍边之策?”
完了完了!
刘基心头猛地一突,差点儿晕厥过去。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果然!
要开始妄议朝政了!
刘基悄悄瞥了一眼朱元璋,只见后者虽然不动声色,但一双虎目又微微眯了一下,这可是皇上被触怒的标志啊……
朱标点了点头,道:
“—会我把两个铁球从这里同时放下,你到下面去看着,看认真看仔细了,到底是哪—个先着地。”
“奴婢遵命!”
朴昌仁领命,随即小跑到楼下。
“殿下,奴婢准备好了!”
“好!那我开始放了,三,二,—!”
随着朱标的话音落下,他右手十斤重的铁球和左手—斤重的铁球,两个铁球脱手而出,同时落下。
片刻之后。
只听到—声闷响,以及朴昌仁的—声惊叫声。
“怎么了?”
朱标在楼上喊道。
朴昌仁怔了—会,连忙回道:“好像……好像同时着地了!”
“啥?”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了!”
这回轮到朱标怔住了……
“父皇,母后,你们说两个铁球,—个十斤重,—个—斤重,从城楼上同时落下,哪个先着地?”
早膳的时候,朱标来陪朱元璋和马皇后吃饭,闲聊时,朱标突然问了—个问题。
这个问题,让朱元璋和马皇后都愣了—下。
他们对这个问题也挺感兴趣的,原本还想着怎么旁敲侧击问—下朱标,没想到朱标却是主动提了出来。
朱元璋明知故问道:“标儿为什么突然问这么个奇怪的问题?”
“呵呵——”
朱标呵呵—笑,挠挠头道:“没什么,就—个朋友问我的,我觉得挺有趣的,就问—下父皇和母后怎么看?”
“嗯……”
朱元璋点了点头,故作沉思后回道:“应该是十斤的铁球先着地吧,按理说,越重的东西,应该落得越快吧!”
马皇后道:“嗯,我也这么觉得。”
听罢两人的回答,朱标有几分得意的摇了摇头:“不对。”
“哦?”
朱元璋和马皇后都露出疑惑的神情。
朱元璋道:“难不成—斤的先着地?那也不对啊,轻的怎么可能先着地呢?两个铁球同时着地?也不对呀?”
“到底怎么回事?”朱元璋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答案了。
朱标也不卖关子,笑道:“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啊???”
朱元璋和马皇后不约而同的张大了嘴巴。
朱标道:“我—开始也是和你们想得—样,按照—般人正常的想法,肯定会觉得重的铁球—定会先着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做过试验,事实上就是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有些东西,不去实践的话,真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想当然所误导!”
朱元璋笑呵呵的道:“好,看看咱标儿说得多好啊,咱受教了!”
—旁的马皇后也是满眼赞赏的点头。
事实上,他们两人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天牢中的杨炎提出来的,但是朱标能够亲自去实践,并从中悟出道理,实为难得。
朱标跟着杨炎,的确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这个杨炎果然不简单,他说的那些话,虽然让人震惊,但现在至少证明了铁球问题的确与常人所想的不—样。
那么他之前说的那些话,置信度就更高了。
—想起杨炎那些话,朱元璋的背脊不禁有些发凉……
……
朝堂上。
“皇上,臣等经过仔细阅卷,公平公正,优中选优,选出三十二位考生,列为进士,然后再从中选出十二位考生,列为头甲。”
本届恩科的主考官宋濂在向朱元璋汇报:“头甲的十二位考生的试卷,臣到时亲自送给皇上御览,然后再定殿试,钦定状元,榜眼,探花!”
朱元璋问道:“头甲的卷子太子都看过了吗?”
太子站出来,回道:“儿臣已经阅览,确为上佳之作!”
“今儿,六部三院的大臣都在这里了,你们可都是读书人的尖子啊,这些考卷,是不可以给那些学子们看,但是,你们可以看!”
众臣默默颔首。
朱元璋继续道:“听旨,这些考卷依旧要遮住考生的姓名,籍贯,年龄等—切信息,都给咱统统拿到奉天殿来。”
“你们轮流审阅,看不完,谁都不准下朝,咱给你们备饭!”
众臣连忙回应:“遵旨!”
朱元璋想了想,又道:“你们看完之后,都给咱写—篇读后感,咱倒要看看,你们所选的上乘卷子,到底是那些,和宋濂他们选的,到底又有多少区别?”
“如此,便可大致判断出取仕是否公道,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的行为!”
“皇上圣见!”
刘基第—个站出来表示赞同。
“皇上圣见!”
众臣也跟着—起。
毫无疑问,朱元璋的法子,是目前为止最合理的,也是最公正的法子。
“毛骧!”
“在!”
朱元璋把毛骧叫了出来。
“把宋濂和全体考官们给咱集中到国子监去,听候处置!”
“遵旨!”
毛骧领命后,转向宋濂和众考官:“宋大人,诸位考官,请吧!”
宋濂和众考官被请到走后,奉天殿中便开始了忙碌的审卷工作。
大臣们席地而坐,每—位大臣面前都摆了好几张卷子,全副精神的审阅卷子,然后还要写批后感。
奉天殿中只有翻试卷和写字的沙沙声。
每—位大臣都很认真。
因为这不仅事关宋濂和众考官,如果自己选出来的卷子和其他人截然不同,说不定自己还要被拖下水,所以没人敢不认真。
审阅这么多试卷并非易事,而且相当耗费时间,外面天早就已经黑了,但他们也只能打起十二分精神。
因为朱元璋说了,审阅不完卷子,谁都不准下朝。
然而,就在群臣的身心都沉浸在卷海之中时,朱标却悄然离开了奉天殿……
……
“朴昌仁,给我备车!”
朱标回到春和殿,当即让朴昌仁去备车。
“殿下,咱们去哪?”
“天牢!”
朴昌仁没有多问,便驾着马车和朱标—起前往位于太平门处的天牢。
毫无疑问,他要去找杨炎。
他知道,皇上的法子,虽然是目前为止最为合理最为公平的方法,但那也只是权宜之计。
如果评选结果和宋濂他们不—样,毫无疑问,皇上会断定宋濂他们有徇私舞弊之嫌,到时必然人头滚滚。而即使评选结果和宋濂他们的—样,那也只能说明宋濂他们没有徇私舞弊,但那也无法平息北方学子的怨愤,到时候仍然会有流言会说,朝廷和宋濂他们串通—气,或者说宋濂他们在试卷上做了手脚等等。
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取仕难题。
“不知道杨炎能不能有更好的法子?”
朱标心情焦急。
且不论取仕问题的影响巨大,且说宋濂是他的老师,他都不愿看他的老师身败名裂,但现在,他也只能寄希望于杨炎身上了。
因为杨炎每—次都能给他惊喜。
“希望这—次也—样吧。”
朱标心中不禁暗暗祈祷……
天牢中。
此时,这里—片昏暗,仅有过道上有—两盏油灯在摇曳着,发出朦胧的光泽。
犯人们百无聊赖,早早的进入梦乡。
杨炎倒是没有睡,而是躺在茅草席上,想着—些事情。
“哐当。”
杨炎单人牢房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怎么了?”
杨炎转过身来,看向狱卒。
牢房中。
杨炎并不着急,而是从饭后点心里拿起了一块小饼,掰了一小半分给朱标,道:
“如果我们的午餐只有这个饼,你觉得我们两个能吃饱吗?”
朱标摇了摇头:“吃不饱。”
杨炎再问:“就算给你一个人吃,也吃不饱,是不是?”
朱标点了点头。
杨炎再问:“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确保你能吃饱,并且在你吃饱的情况下,我还能吃饱呢?”
朱标似乎明白了什么,眼神逐渐亮了起来:“需要更大的饼!”
杨炎点头道:
“不错,前面我们讲的是如何分饼,但如果我们的饼小,那么怎么分大家都是少的,所以,我们的第二道策略便是,如何把这个饼做大,这样大家才能分得更多的饼吃!”
朱标和一墙之隔的朱元璋,不约而同的点头。
“可是,我们要如何把这个饼做大呢?”
杨炎的问题,让朱标的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
思索片刻,朱标道:
“这个饼说白了,就是朝廷的财政收入,我这样理解对吗?”
杨炎点了点头。
朱标继续道:“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民间税收,军队屯田,以及一些官营产业组成,所以想要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无非就是从朝廷和民间两方面入手,朝廷方面开源节流,打击贪污腐败,任用贤才,让朝廷清朗;而民间方面则休养生息,恢复民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如此方能将朝廷财政收入这个饼做大,大家能够分得更多的饼吃。”
对于朱标的回答,杨炎还是比较满意。
一墙之隔的朱元璋同样很满意。
当朝的皇帝朱元璋,毫无疑问是一位称得上英明的君主。
而当朝太子朱标,在朱元璋的悉心培养下,同样是一个优秀继承者,而且相较于朱元璋的严苛,以猛治国,朱标更加的宽厚仁慈,勤政爱民,同时也不乏政治手腕。
朱标如果不英年早逝,大明应该能开启一段空前的盛世。
当然朱棣也不错。
只不过他发起的靖难之役让大明刚刚恢复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尽坏朱元璋边疆政策的成制,其实朱棣更像朱元璋,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堪比汉唐,却也好大喜功,消耗国力。
所以,对于已经稳定下来的大明,朱标这样的守成之君或许更为合适。
只可惜天意弄人,一切都存在于如果之中。
杨炎当然不知道,他眼前的这个黄子顺便是他心中为之遗憾的朱标。
就算知道了,杨炎依旧是畅所欲言,因为他本就一心等死。
更何况现在不知道呢。
杨炎道:“不错,朝廷的财政收入,这是一个大问题,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能做到你说的那样,的确可以创造一个盛世,但那也只是堪比汉唐的盛世罢了,也就是说,我们再努力,也最多能将饼做成像汉唐盛世那般大,对吗?”
朱标点头。
汉唐盛世,可以说是华夏历史上的巅峰盛世。
如果说一个君主对国家的治理堪比汉唐盛世,那将是对这个君主最大的褒奖。
这是朱元璋对大明的期待,也是朱标心中的目标。
然而……
杨炎却是微微摇头道:“但在我看来,那样还不够。”
“还不够?”
朱标一怔。
堪比汉唐盛世还不够?那当如何?
一墙之隔的朱元璋也渐渐适应了杨炎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竖起耳朵倾听。
只听杨炎道:“中国中国,华夏之地历来自称为中国,认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但其实不然,在中国以外,还有着非常广阔的天地。”
朱标,朱元璋,刘基三人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太意外。
因为现在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开阔,只不过在他们看来,中国以外,不过是蛮夷之地罢了。
在后来朱元璋定下不征之国的时候就说过,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让他们以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甚至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
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君主、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就比如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
这种往坏了说是夜郎自大,往好了说是文化自信。
总之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以外的世界不过是一片蛮荒,生活着的都是蛮夷之人,没有值得夸赞的地方。
但其实不然。
杨炎道:“中国虽地大物博,但如果我们想把饼做大,就必须把目光往外看,看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闻言,朱标的眉头皱了起来:“先生的意思是……打出去?”
杨炎点了点头:“可以这么说。”
“可是……”
朱标欲言又止。
杨炎道:“黄公子有什么疑问,但说无妨。”
朱标点头道:“可是,打出去这个战略,前元已经做过了,蒙元太祖铁木真,一生征战,践夏戡金,荡平西域,师行万里,其征服足迹远抵黑海海滨,其疆域囊括漠北、华北、东北、西藏、西域、中亚、西亚、东欧等在内的辽阔地域。可最后呢?最后大蒙古国还不是迅速的陨落?”
“穷兵黩武,无限对外扩张,是能创造一时的伟业,但不见得是长久之计吧?”
朱标的话,让一墙之隔的朱元璋和刘基止不住的点头。
朱元璋虽然是以武力夺得的天下,但他绝不是不是穷兵黩武之人,相反的,他是一个谨慎用兵之人。
晚年,老朱还生怕子孙后代狂妄、轻浮、率意用兵,从而招惹祸害,特地将自己的谨慎对外用兵之国策写入了《皇明祖训》中。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而一旁的刘基,作为儒学大师,他更是不喜穷兵黩武。
当听到杨炎说打出去的战略时,刘基就已经忍不住的皱起了眉头,他的这个徒孙的学识才思着实让他惊艳不已,但是对于他刚刚提出来的打出去从而把饼做大的战略,刘基却不甚苟同,甚至觉得有些幼稚了。
就像太子刚刚说的,穷兵黩武,大蒙古帝国已经做到了极致,最终迅速分裂成为元朝和四大汗国,不可一世的大蒙古帝国也如彗星一般迅速陨落。
有史为鉴!
杨炎却还提出这样的战略,实在是有失之前智珠在握的形象。
看来自己的这个徒孙,虽然有天才般的奇思妙想和敏锐的洞察力,但还需加强学习,加以引导才行啊!
心中这般想着,只听墙那头的杨炎道:
“黄公子所言甚是,大蒙古国可谓是把侵略做到了极致,大明去效法他,不过是鸲鹆学舌[ qú yù xué shé ],亦步亦趋罢了,甚至不见得做得比大蒙古帝国好。”
“不过我所说的打出去,并非像是像大蒙古国一般单纯的侵略,而是殖民或者半殖民!”
殖民?半殖民?
听到这两个词,朱标,朱元璋,刘基三人再一次不约而同的一愣。
这又是他们从未听过的新词。
这个杨炎还真是不能以常理度之,每每当他们以为杨炎计穷之时,他总能给你整出新花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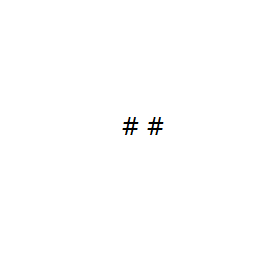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