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陈修远苏信的其他类型小说《寸脉藏春秋全局》,由网络作家“辰砂墨”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第一章:墨影灯昏建安四年深秋,南阳郡的夜风卷着杏叶掠过青蚨堂的飞檐。十八岁的苏信趴在桐木案上,狼毫笔尖在羊皮纸上洇开墨团,《难经・十八难》里“脉有三部,部有四经”的字句在油灯下晃成重影。他揉了揉发酸的手腕,忽然听见隔壁诊室传来粗重的喘息声。“王阿婆这脉,左寸浮滑如珠走盘,右关沉缓似泥裹絮。”师父陈修远的声音混着捣药的笃笃声传来,“寸为肺,关为脾,肺有痰浊,脾失健运,当用二陈汤加炒白术——秋时,去库房取三钱制半夏。”苏信应了一声,却盯着自己抄录的《黄帝内经》脉诀图出神。图上红笔标着“上部天候头角,中部人候心主,下部地候肾经”,二十三处脉位星罗棋布,与《难经》里“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截然不同。他摸着腰间磨旧的牛皮脉诊袋,...
《寸脉藏春秋全局》精彩片段
第一章:墨影灯昏建安四年深秋,南阳郡的夜风卷着杏叶掠过青蚨堂的飞檐。
十八岁的苏信趴在桐木案上,狼毫笔尖在羊皮纸上洇开墨团,《难经・十八难》里 “脉有三部,部有四经” 的字句在油灯下晃成重影。
他揉了揉发酸的手腕,忽然听见隔壁诊室传来粗重的喘息声。
“王阿婆这脉,左寸浮滑如珠走盘,右关沉缓似泥裹絮。”
师父陈修远的声音混着捣药的笃笃声传来,“寸为肺,关为脾,肺有痰浊,脾失健运,当用二陈汤加炒白术 —— 秋时,去库房取三钱制半夏。”
苏信应了一声,却盯着自己抄录的《黄帝内经》脉诀图出神。
图上红笔标着 “上部天候头角,中部人候心主,下部地候肾经”,二十三处脉位星罗棋布,与《难经》里 “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 截然不同。
他摸着腰间磨旧的牛皮脉诊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九根辨脉银针,那是去年随师出诊时,陈修远亲自为他打磨的。
“又在琢磨三部九侯?”
青布衫角带过一阵艾草香,陈修远不知何时站在屏风后,手中握着半卷竹简,“明日城西刘老翁复诊,你且用《内经》之法诊脉,我在旁看着。”
第二日辰时,刘老翁扶着枣木拐杖进门,鬓角沾着晨露:“昨夜头痛如裂,似有锥子凿额角。”
苏信忙扶他躺上竹榻,先以食指轻触其额角动脉 —— 上部天脉,应手而搏,数急如雀跃。
再移至颊车穴处,下部地脉弦紧如弓弦。
接着按察合谷、神门、太溪,指尖在二十三处脉位间辗转,额角渐渐沁出细汗。
“上部天脉数,主风热上攻头面;中部人脉涩,主心血不足;下部地脉弦,主肝风内动……” 苏信沉吟着铺开宣纸,尚未写完,陈修远已坐在脉枕前,三指轻落患者寸口:“左寸浮数,右关弦滑,尺部沉弱。
寸为阳,主上焦,风热袭肺则皮毛不固,风邪循经上犯清空;关为中,弦滑属肝脾,土虚木乘则生内风 —— 病在肺肝,根在脾虚。”
老翁突然剧烈咳嗽,震得竹榻作响。
苏信慌忙去扶,却见陈修远从袖中取出银针,认准列缺、合谷、足三里,银芒闪处已刺入三分:“昔年扁鹊过赵,尝言‘圣人
鱼身上,正刻着“独取寸口”四个泛着青光的大字。
第三章:白河惊浪白河码头的风带着刺骨潮气,立冬前的河面已漂着碎冰。
苏信跟着陈修远踏过湿滑的跳板时,船工李三的咳喘声像破了洞的风箱,从舱底闷闷传来。
“郎中救命!
我家男人腿肿得像水桶,昨夜咳得吐了血!”
李三媳妇掀开舱帘,鬓角沾着水草,衣襟上还滴着河水,“找了三个大夫,都说是什么‘水蛊’,开的都是逐水药,喝了反而喘得下不了床。”
舱内浊气熏蒸,李三半靠在草席上,面色青白如纸,双腿肿胀发亮,按之凹陷难起。
苏信刚要伸手诊脉,忽见他喉头一紧,喷出半口鲜血,染红了胸前粗布衫。
“莫慌。”
陈修远按住苏信发颤的手腕,指尖先触李三额角——上部天脉微浮而散,如落絮漂水;再按颊车穴,上部地脉壅塞如泥;接着是合谷、神门,中部人脉细如发丝,按之即无;太溪穴处的下部地脉,沉伏如石沉渊,需推筋着骨才能寻到一丝搏动。
“上部天脉散,主阳气外越;地脉壅,主水湿上泛;中部人脉绝,心阳将脱;下部地脉伏,肾水凝冰……”苏信的声音有些发抖,二十三处脉位的脉象在脑海里乱作一团,“这、这该如何是好?”
陈修远却已坐在李三身侧,三指轻落寸口。
舱内光线昏暗,苏信却看见师父指尖在脉枕上微微发亮,如同夜航船望见灯塔。
“寸脉微迟如羹汤冷透,关脉芤虚似空谷传声,尺脉伏匿若寒潭结冰。”
他忽然抬头,“取艾条,灸关元、气海,快!”
李三媳妇慌忙从药箱里翻出艾绒,苏信手抖得几乎点不着火。
陈修远却已解开患者衣襟,在脐下三寸处悬灸,艾烟缭绕中,李三的喘息竟渐渐平顺。
“寸为宗气所聚,微迟是大气下陷;关为脾胃之主,芤虚是土不制水;尺为肾命之门,伏匿是水火不济。”
他边施灸边说,“逐水药虽能泄浊,却伤了脾肾之阳,如今阳气将脱,当以‘塞流’为先。”
苏信盯着师父手下的寸口脉,忽然想起《难经·十四难》里“脉有根本,人有元气”的句子。
方才他遍诊九侯,被二十三处脉象迷了眼,却没看见最关键的寸口脉已露出“根气将断”的征兆——就像
那方刻着寸关尺的紫檀脉枕推到明哥儿面前,“先练指下能分浮中沉三候,再辨寸关尺三部,最后合二十七脉于一体——就像你师祖说的,把满天星斗收进玉壶,壶中自有乾坤。”
更鼓初响,青蚨堂的铜铃在晚风中轻晃。
苏信站在廊下,望着后园里陈修远亲手栽的杏树,枝桠间挂着明哥儿新晾的脉诊袋,在月光下轻轻摇曳。
他摸了摸袖中那方刻着“独取寸口”的玉牌,忽然听见诊室传来明哥儿的惊呼:“师父,这寸脉浮数,关脉弦滑,不就是前日船工李大叔的脉象吗?”
笑声混着杏花香飘出窗外,苏信忽然看见时光重叠——当年那个在雨夜苦读《难经》的少年,那个在白河码头手忙脚乱的学徒,此刻都化作了小徒弟眼中的星光。
而中医的智慧,就像这年年盛开的杏花,在寸口脉的方寸之间,在师徒相授的墨香之中,在无数个望闻问切的清晨与黄昏,永远带着新生的希望,次第绽放。
尾声三十年后,南阳郡志多了一笔:“青蚨堂苏信,精研《难经》寸口脉法,著《脉简》三卷,言‘三部九侯如江河入海,寸口一脉便是波澜’,活人无数。”
而在青蚨堂的后室,明哥儿正教着自己的徒弟辨认脉枕:“这寸关尺,寸候天,关候人,尺候地,合起来便是天地人三才……”阳光穿过雕花窗棂,照见脉枕上深深浅浅的刻痕——那是三代医者的指纹,也是中医千年传承的印记。
杏花瓣落在《难经》残卷上,“独取寸口”四字在春光里泛着微光,仿佛在诉说:医道的智慧,从来不在遍寻枝叶的繁茂,而在深扎根本的笃定。
就像这腕间的一脉搏动,连着的不仅是心肺脾肾,更是古往今来医者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望。
中焦虚寒;尺为肾,沉弱是命门火衰,不能暖脾。”
<老妇突然剧烈呕吐,清水混着白沫溅在苏信鞋面上。
他正要去取毛巾,却见陈修远从袖中掏出温针,在老妇足三里、内关、风池三穴施针,艾绒燃烧的青烟里,老妇眉间的皱纹渐渐舒展:“她头痛虽在上,病根却在中焦。
前日王郎中见呕吐便用吴茱萸汤,却不知弦细脉主肝虚,过用温燥反伤肝阴——这便是‘舍症从脉’的道理。”
药煎好时,晨雾已散,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师父身上镀了层金边。
陈修远将药碗递给张媒婆,忽然转向苏信:“你用三部九侯法,诊出风热、胃热、心血虚、脾肾阳虚,看似周全,却如撒网捕蝶,网眼太密反而失了重点。”
他以银针尾端轻点脉枕上的寸关尺标记,“寸口脉分三部,每部候三候,浮沉迟数间便知病在何脏,邪正如何——就像看天上星,不必数清每颗,只需辨明北斗方位。”
苏信望着老妇喝药时舒展的眉头,忽然想起《难经》里“寸口者,脉之大会”的句子。
昨日他还觉得三部九侯法如满天星斗,此刻却见师父在寸口脉上轻轻一拨,便拢住了最重要的北斗七星。
“明日随我去白河码头。”
陈修远收拾银针时,忽然瞥见苏信袖口的墨渍,“那里有位船工患水肿,遍身脉位如乱麻,你且用两部法试试,看是古法周全,还是寸口脉简便。”
暮色漫进诊室时,苏信独自坐在案前,将今日的脉案与师父的诊断对比。
他发现自己记录的二十三处脉位,竟有十七处能在寸关尺上找到对应:上部天的数急是寸脉浮紧,中部人的细涩是关脉弦细,下部地的沉迟是尺脉沉弱——原来三部九侯的玄机,从未离开过这寸口三分。
更鼓敲过二更,苏信摸着脉枕上师父新刻的寸关尺纹路,忽然明白:医理如江河,有的流于地表,可见百川归海;有的潜入地下,可探泉眼源头。
师父并非摒弃古法,而是在二十三处脉位中,寻到了能照见全身的那面镜子。
这一夜,青蚨堂后的杏树落了满地金黄,苏信梦见自己站在白河畔,看见无数脉象化作游鱼,而师父的三指如渔网,轻轻一兜,便将最深处的那条大鱼捞起——那
在乱麻中找线头,师父却直接握住了寸口这端,轻轻一拉便解开了死结。
艾条燃尽第三支时,李三忽然咳出一口清稀痰液,眼睑动了动。
陈修远这才擦了擦额角的汗,从袖中取出《难经》残卷,借舱口微光翻开:“你看这‘损脉’之说——‘一损损于皮毛,二损损于血脉,三损损于肌肉,四损损于筋,五损损于骨’。
李三水肿咳喘,看似病在肌表水湿,实则五损已及骨髓,故尺脉伏匿,此为‘阴阳离决’之兆。”
河水拍打着船帮,苏信忽然想起上个月在医案里见过的“水肿忌攻”条:“师父是说,观寸口脉可知病损程度,不必遍寻九侯?”
“非也。”
陈修远指尖划过竹简上的“寸关尺”图示,“三部九侯如观全局地图,寸口脉则是地图上的指南针。
李三的太溪脉伏匿,合谷脉细绝,这些在寸口脉上早有预兆——左尺候肾,伏匿是肾精竭;右关候脾,芤虚是脾阳亡。
你遍诊时被上部的浮散脉迷惑,却忘了‘有胃则生,无胃则死’,关脉的胃气已虚,才是致命之由。”
船工媳妇端来热姜汤时,晨光正穿透河雾,在陈修远袖口染了层金边。
苏信望着师父为李三重新诊脉的手,忽然明白:三部九侯法是“知其然”,而寸口脉法是“知其所以然”——就像庖丁解牛,初时见全牛,久了却能见筋骨脉络,刀刃所至,正是关键处。
“明日起,你每日随我练‘三部九候归寸口’。”
陈修远收拾药箱时,将一根刻着寸关尺的檀木脉枕塞进苏信手中,“把二十三处脉位的脉象,都对应到寸关尺上,就像把散钱串成串,用时便得心应手。”
归程中,白河的浪花拍打着岸石,苏信摸着脉枕上凹凸的纹路,忽然想起《难经》里“寸口者,五脏六腑之所终始”的话。
原来古人创制三部九侯法,是为了穷尽脉理;而《难经》独取寸口,是为了在穷尽之后,找到最直接的法门——就像星辰归位,百川入海,最终都落在这三寸腕间的波澜里。
这一夜,青蚨堂的灯火又亮到三更。
苏信在脉案上画下李三的寸口脉象,左寸微迟如霜,右关芤虚似雾,尺部伏匿若深渊——他忽然懂得,所谓“独取寸口”,不是舍弃,而是凝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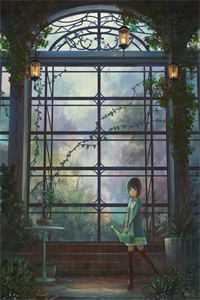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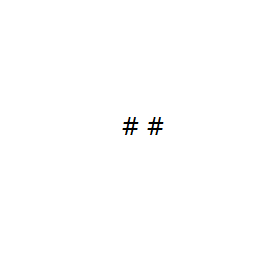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