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都市连载
热门小说《时日不多,独自流浪》是作者“山葡萄”倾心创作,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这本小说的主角是韩冰李姐,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在生命倒计时,一个早已习惯被生活遗弃的19岁少年,如何以最低的姿态、最沉默的方式,完成一场只属于自己的、向内的生命体验与告别。摒弃宏大叙事与戏剧转折,聚焦于微小、真实、充满呼吸感的日常细节,展现一个普通灵魂在绝境中寻求宁静与自由的独特旅程...
主角:韩冰李姐 更新:2025-06-19 13:31:00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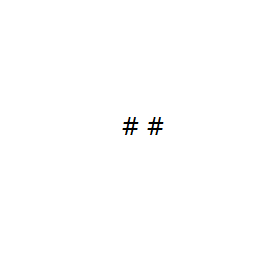
男女主角分别是韩冰李姐的现代都市小说《时日不多,独自流浪无广告》,由网络作家“山葡萄”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热门小说《时日不多,独自流浪》是作者“山葡萄”倾心创作,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这本小说的主角是韩冰李姐,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在生命倒计时,一个早已习惯被生活遗弃的19岁少年,如何以最低的姿态、最沉默的方式,完成一场只属于自己的、向内的生命体验与告别。摒弃宏大叙事与戏剧转折,聚焦于微小、真实、充满呼吸感的日常细节,展现一个普通灵魂在绝境中寻求宁静与自由的独特旅程...
韩冰靠墙站着,后背紧贴着冰凉的、带着些许污渍的瓷砖墙壁。他手里捏着社区诊所开的转诊单和挂号单,纸张的边缘已经被他无意识揉搓得有些发软。太阳穴的钝痛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还在一下下缓慢地拉扯着他的神经,每一次心跳都加剧着那份沉闷的压迫感。视野的边缘时不时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模糊,像老电视信号不稳时的雪花点,一闪即逝,却足以让他心头一沉。他微微低着头,额前汗湿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部分视线,也隔绝了周围一些过于直接的、带着探究或麻木的目光。他把自己缩进一个无形的壳里,尽量不去看那些痛苦的面孔,不去听那些悲戚的声音。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一种生理性的不适和更深沉的疲惫。他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拿到一个答案,无论是好是坏,然后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
“韩冰!韩冰在不在?韩冰!” 一个穿着粉色护士服、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写满疲惫眼睛的护士,举着手里的单子,提高了音量在分诊台附近喊着。
韩冰身体微微一震,抬起头,哑着嗓子应了一声:“在。”
“这边!神经内科急诊3诊室,李医生!” 护士语速很快,手指了指走廊深处一个方向,目光在他苍白得有些过分的脸上停留了半秒,随即又投入到下一张单子的叫号中,仿佛刚才那一眼的停顿只是例行公事。
“谢谢。” 韩冰低声说,声音被周围的嘈杂轻易吞没。他捏紧手里的单子,像握着一片即将沉入水底的浮木,朝着护士指示的方向走去。每一步都感觉有些虚浮,踩在光洁冰冷的地面上,发出轻微却空洞的回响。走廊两侧的诊室门大多紧闭着,偶尔打开一条缝,能瞥见里面穿着白大褂的身影和躺在检查床上的病人,随即又迅速关上,隔绝出一个个微小而沉重的世界。
3诊室的门虚掩着。韩冰在门口停住脚步,深吸了一口那混合着消毒水和绝望的空气,屈起手指,轻轻敲了两下。
“请进。” 里面传来一个中年男人平稳、略显沙哑的声音,带着职业性的冷静。
韩冰推门进去。诊室不大,布置简单。一张宽大的、铺着白色无纺布的诊疗床靠墙摆放,旁边是各种闪着冷光的检查仪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占据了主要位置,上面堆满了病历夹、检查申请单、笔筒和一个巨大的、造型略显笨重的电脑显示屏。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男医生,戴着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锐利而疲惫,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仿佛永远在思考着什么难题。他穿着干净但有些发皱的白大褂,胸牌上写着“李振华 副主任医师”。
“韩冰?” 李医生抬起头,目光透过镜片落在韩冰脸上,没有多余的情绪,像在审视一件需要修理的物品。
“是。” 韩冰走到桌前,将手里的转诊单和挂号单递过去。指尖冰凉。
李医生接过单子,低头快速扫了一眼社区诊所潦草的记录:**“反复剧烈头痛伴视物模糊、呕吐月余,加重一天。建议头颅影像学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 他拿起鼠标,在电脑上点了几下,调出韩冰刚才在急诊影像科做的头颅CT扫描结果。屏幕上瞬间跳出一幅幅灰白相间、结构复杂的脑部断层图像。
诊室里很安静,只有电脑主机风扇低沉的嗡鸣和空调冷气出风口嘶嘶的送风声。空气比走廊里更加冰冷干燥,带着一股金属和塑料的混合气味。韩冰站在桌前,像等待审判的囚徒,目光落在医生身后墙上挂着的复杂神经解剖图上。那些盘根错节的血管和神经,此刻看起来像一张预示厄运的蛛网。
李医生的目光在电脑屏幕和手中的纸质报告(影像科出具的初步诊断意见)之间来回移动。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轻微而规律的“哒、哒”声。镜片后的眼神变得越来越专注,眉头也锁得更紧。他拖动鼠标滚轮,反复放大、缩小着屏幕上的某个区域,鼠标点击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被拉长、灌满了铅。韩冰能清晰地听到自己血液在太阳穴附近血管里奔流的声音,那沉闷的搏动与持续的钝痛交织在一起。他垂在身侧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指甲掐进掌心,带来一丝尖锐的刺痛,试图驱散那不断蔓延的冰冷麻木感。
终于,李医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再戴上时,目光直直地看向韩冰。那目光不再是审视,而是一种带着沉重事实的、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韩冰,” 李医生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根据你的CT扫描结果,结合你的症状,情况…不太好。”
他拿起那张影像报告,推到韩冰面前,手指点着上面打印出来的一幅最关键的影像图片。韩冰的目光落上去。在一片灰白相间的脑组织影像中,右额叶深部靠近基底节区域,赫然嵌着一个边界不清、形状不规则的深灰色团块影。它像一个恶意的寄生体,盘踞在那里,周围的组织似乎被挤压、扭曲,环绕着大片不规则的、颜色更浅的阴影(水肿带)。
“这里,” 李医生的指尖精准地落在那团深影上,“长了一个肿瘤。位置非常不好,在额叶深部,靠近重要的神经传导束和血管区域。从影像学的形态、密度和周围水肿情况来看…”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最终还是选择了最直接的医学表述,“**高度怀疑是恶性胶质瘤,WHO分级IV级,也就是…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
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铁钉,被李医生用平静的语气,一根一根地钉入韩冰的耳膜,再狠狠凿进他的脑海深处。
“恶性…胶质瘤?” 韩冰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这个陌生的名词,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他看着屏幕上那个丑陋的深色团块,那就是潜伏在他头颅里、正疯狂吞噬一切的恶魔吗?他感觉不到愤怒,也感觉不到悲伤,只有一种巨大的、荒谬的不真实感。这怎么可能?他才十九岁,刚刚撕碎了一张可能改变命运的纸片,他还在计算着下一顿如何省下两块钱。
“对。这是成人中最常见、也是最具侵袭性、恶性程度最高的原发性脑肿瘤。” 李医生的语气没有任何起伏,像是在宣读一份客观的病理报告,“它的特点就是生长极其迅速,呈浸润性生长,就像树根一样,会深入到周围正常的脑组织里,很难完全清除。而且,它所在的位置…” 他的指尖再次点了点屏幕,“靠近运动、感觉和语言功能区,也毗邻重要的供血动脉。手术风险…极高。”
他拿起鼠标,点开另一张放大的图像,指着肿瘤周围那些颜色更浅的区域:“看这些,是明显的水肿带。肿瘤本身和水肿会不断压迫、侵蚀周围的正常脑组织,这就是你剧烈头痛、呕吐和视物模糊的根本原因。随着肿瘤增大和水肿加重,症状会越来越严重,可能出现肢体麻木无力、抽搐、言语不清,甚至意识障碍。” 他的描述冰冷而具体,像一把解剖刀,精准地剖开韩冰身体里正在发生的灾难。
韩冰的目光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个象征死亡的影像,大脑一片空白,只有医生那些冰冷的专业术语在里面嗡嗡作响:恶性、最高、侵袭性、风险极高…每一个词都在碾碎他仅存的、微弱的侥幸。
“那…能治吗?”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问,遥远得不像自己的,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陌生的平静。仿佛在问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李医生看着他过于平静的脸,镜片后的目光似乎闪过一丝极微弱的波动,但很快又恢复了职业性的冷静。他重新坐直身体,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治疗…非常困难。” 他坦诚地说,“标准的治疗方案是最大程度的安全手术切除,尽可能多地移除肿瘤组织,减轻压迫,然后立即进行同步放化疗(放疗结合替莫唑胺化疗),之后再持续几个周期的辅助化疗。这是目前能最大限度延长生存期的方式。”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给韩冰消化信息的时间,然后继续用那种平稳而客观的语调陈述着冰冷的现实:
“但是,第一,手术风险。位置太深,涉及功能区,术中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偏瘫、失语、失明等严重残疾。而且,由于它的浸润性,手术不可能彻底清除干净,显微镜下甚至更远处都会有残留的肿瘤细胞。第二,放化疗的副作用。放疗会对正常脑组织造成损伤,可能引起认知功能下降、疲劳、脱发等。化疗药物(替莫唑胺)有骨髓抑制(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导致感染和出血风险)、恶心呕吐、肝肾功能损伤等副作用。第三,复发。即使经过标准治疗,这种肿瘤的复发率也几乎是百分之百,而且复发后进展更快,更难控制。第四…费用。” 李医生拿起笔,在韩冰那张挂号单的空白背面快速写下一串数字:
* 开颅手术及住院费(预估):8-12万*"
果然…如此。
他对着镜子里的人,无声地翕动了一下嘴唇。像是在嘲讽,又像是在确认一个早已心知肚明的事实。命运从未对他仁慈过哪怕一次。每一次当他以为终于抓住了一根稻草,哪怕再细弱,命运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其碾碎,再将他推入更深的泥潭。父母的离弃是第一次,生活的重压是漫长的第二次,而现在,这具躯体的背叛,是最终也是最彻底的第三次。连挣扎的力气,都早已在漫长的消耗中消失殆尽。
他扯过那条搭在椅背上的旧毛巾——它原本就带着油污和汗味——胡乱地擦干头发和脸,动作粗暴,仿佛在擦拭什么肮脏的东西。然后,他走到桌边,拉开那张吱呀作响的塑料凳,坐了下来。冰冷的凳面激得他皮肤一紧。
目光落在桌面那四张纸上,最终,定格在那张皱巴巴的通知书上。“学费标准:5800元/学年”。那串数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视网膜上。他移开目光,拉开桌肚,从一堆螺丝钉、旧电池和几张皱巴巴的超市小票下面,翻出那个小学生用的、红色塑料封皮的廉价计算器,还有一支快写不出水的圆珠笔和一本巴掌大小、封面印着“收支明细”的软皮抄——那是他用来记录每一笔收入和支出的账本,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
他拿起笔,笔尖在纸上划拉了几下,才艰难地渗出一丝墨迹。他翻开账本新的一页,没有看之前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直接在最上方写下今天的日期。然后,他开始计算,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只垂死的蚕在啃食桑叶。
支出:
*社区诊所挂号 + 开转诊单:¥15.00** (他清晰地记着数字)
*市一院急诊挂号 + CT检查:¥268.50*(口袋里剩下的零钱证实了这一点)
*止痛药(布洛芬缓释胶囊,在医院外药店买的):¥18.80*(瓶子上贴着价签)
*收入:无
他停下笔,看着这三笔支出。302.3元。这是他今天为确认自己的死亡日期所付出的代价。一个冰冷的数字,换取另一个更冰冷的数字:三个月。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转瞬即逝的弧度,像是在嘲笑这荒谬的等价交换。
然后,他的笔尖移向下方,另起一行。这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笔尖在纸上快速移动,每一个数字都带着冰冷的重量。
总计:23200 (学费) + 4800 (住宿) + 3200 (书杂) + 16200 (在校生活费) + 9000 (假期生存费) + 560 (路费) = 56960元。
看着纸上那个最终的数字:*56960*。韩冰的呼吸微微一滞。比他之前在医院门口心算的还要高出近一万块。这几乎是把他自己当成一台永不停歇、无需维护的机器,才能勉强维持的底线预算。没有意外,没有疾病,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没有买一件新衣服的可能,甚至不能多吃一个鸡蛋。
他放下笔,拿起桌上那个老旧的智能手机。屏幕有几道细微的划痕。他点开那个熟悉的银行APP图标,输入密码。短暂的加载后,账户余额清晰地显示在惨白的屏幕上:
¥ 8013.52
一个他用了三年青春,在油烟、汗水、冷眼和疲惫中,一分一厘积攒下来的数字。曾经,这个数字代表着希望,代表着那扇可能通往不同人生的窄门。如今,它被赤裸裸地放在那个庞大的“56960”旁边,像一个微弱的烛火被置于狂风之下,瞬间就显得如此渺小、可笑、不堪一击。
缺口:56960 - 8013.52
三年,他攒下了8千。未来四年,他需要再赚近四万八,才能填上这个无底洞。而且,这还是在没有考虑任何学费上涨、物价波动、以及他自身可能出现的任何状况(比如,像今天这样的“意外”医疗支出)的前提下。
韩冰的目光在“56960”和“8013.52”之间来回移动。像两台冰冷的计算机器在无声地碰撞、运算。他不是没想过助学贷款。但助学贷款只能覆盖学费和住宿费的一部分,而且需要担保人。担保人?脑海中闪过那个空号的提示音和电话里婴儿的啼哭声。他扯了扯嘴角。至于生活费、书本杂费、假期生存费…这些沉重的负担,贷款解决不了。他只能靠自己。靠他这具已经开始发出警报、随时可能彻底罢工的躯体。
一股冰冷的、带着铁锈味的绝望感,如同从脚底蔓延而上的冰水,缓缓淹没了他的心脏。不是激烈的、撕心裂肺的痛苦,而是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缓缓下沉的绝望。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他的喉咙,一点点收紧。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医院CT屏幕上那个狰狞的深灰色团块,李医生那平静却字字诛心的话语在耳边回响:“平均生存期…很难超过14到16个月…五年生存率…低于百分之五…治疗过程本身…会非常痛苦…费用…天文数字…”
治疗?
那个念头只在他脑海中闪过一瞬,就被更冰冷的现实碾得粉碎。手术费8-12万起?放化疗一个疗程10-15万?后续持续不断的无底洞?他这点钱,恐怕连手术的零头都不够。更别提那渺茫到近乎于无的生存希望,以及治疗过程中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尊严的丧失。用这仅有的、维持生存的钱,去换取几个月更痛苦、更毫无质量可言的“活着”?还要背上可能一辈子(如果真有所谓的一辈子的话)都还不清的债务?这笔账,太清晰了。清晰到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放弃治疗。
这个决定,在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在他心里尘埃落定。此刻,面对着这冰冷的数字对比,这个决定变得更加坚硬、更加无可辩驳。不是勇敢,不是洒脱,只是别无选择下最务实、最冰冷的计算。
那么…大学呢?
韩冰的目光缓缓移向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红色的校徽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黯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一个他并不了解、也谈不上喜欢,只是觉得“可能好找工作”而填写的专业。它曾经象征着一个微弱的、改变阶层的可能性。现在,它成了一张通往更沉重枷锁的门票。用他仅剩的三个月生命,去换取四年甚至更久的、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奴隶生涯?为了一个他注定无法到达的未来?
意义在哪里?"
网友评论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