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崇祯王承恩的现代都市小说《完整版大明:距离灭国还有七天?他坐吃等死了》,由网络作家“文盲写小说”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大明:距离灭国还有七天?他坐吃等死了》,是作者大大“文盲写小说”近日来异常火爆的一部高分佳作,故事里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崇祯王承恩。小说精彩内容概述::“邱瑜,你将消极怠工的官员名单整理成册,以升迁为诱饵,让他们每人每天清晨写一份工作计划,将这一天打算做的事全部写下来。”“晚上写工作总结,将计划完成情况进行汇总。完成的在上面画个圈,未完成的要写上未完成的原因。”“写完后将这份工作计划和总结交给你,你再进行求证考核。”“胡编乱写的,不写计划和总结的,所做的事情与职位不符的,全部上书罢免。”......
《完整版大明:距离灭国还有七天?他坐吃等死了》精彩片段
方岳贡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这个办法确实有效,但浪费的银子将是一笔巨款。
李邦华看不下去了,他向前一步躬身施礼:“陛下不可,京师中的奸商见流贼将至运输不畅,纷纷抬高粮价,此乃不法之行为,按律应当予以惩治。用内帑的钱买高卖低看似体恤百姓,实则有...有助纣为虐之嫌。”
其余众人纷纷汗颜。
李邦华太硬气了,竟然当着皇上的面指责皇上助纣为虐。
当御史的时候就屡屡如此,没想到当了内阁首辅更硬气了。
“大胆!”王承恩尖锐的声音响起,“李阁老应该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仗着陛下重用就胡言乱语,休怪陛下无情。”
李邦华毫不畏惧:“陛下,大明律有言,乱世用重典,王道杀伐震慑,法也!此时不用重典,何时用?”
乾清宫针落可闻。
李邦华的话已经不是指责了,而是质问。
质问皇帝为什么不用重典!
崇祯没有生气,反而淡淡一笑:“李阁老怎知我没用重典?”
“可是...”
“朕如果用重典惩治那些商人,一旦消息传出去,还会有商人往京师运粮吗?”
“就算有,运送的数量有之前的几成?”
“京师百万民众每天吃掉的粮食多达上万石,流贼将至,应该广积粮。商人为了暴利,肯定会加速运粮,此举正合朕意。”
“至于银子...,范景文管着京师三大营,只要不让那些商人把银子运出去,朕就有办法将银子拿回来。”
方岳贡和李邦华对视一眼,纷纷汗颜。两人立刻下跪,先是向崇祯请罪,随后领旨谢恩。
“邱瑜!”崇祯将目光看向这位吏部尚书。
“臣在。”
“你说的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普遍吗?”
“回陛下,占京卿总数的三四成。若是人少,臣也不会向陛下请示,早就联合都察院弹劾了。”
崇祯长吸一口气,点点头。
这件事很棘手。
官员们这么做无非是两种心态。
一,京师守不住了,继续做那些事没有什么意义,不如摆烂。
二,只有消极怠工,才能确保京师守不住。这样他们才能送走旧皇帝,迎来新皇帝。
第一种心态的官员还好,属于骑墙派。没有忠心,更谈不上爱国。虽然没干好事,但也没干坏事。
第二种心态的官员最可恨,身在大明心在顺/满清。专门做坏事,扰乱朝堂,搞乱朝政。使政令不通,百姓不满。
既然如此,必须给这帮大明打工人上强度了!
“其他人先出去等待。”
等所有人离开,殿门关闭后崇祯才低声说道:“邱瑜,你将消极怠工的官员名单整理成册,以升迁为诱饵,让他们每人每天清晨写一份工作计划,将这一天打算做的事全部写下来。”
“晚上写工作总结,将计划完成情况进行汇总。完成的在上面画个圈,未完成的要写上未完成的原因。”
“写完后将这份工作计划和总结交给你,你再进行求证考核。”
“胡编乱写的,不写计划和总结的,所做的事情与职位不符的,全部上书罢免。”
“听懂了吗?”
邱瑜站在原地愣了得有三分钟,他扭动僵硬的脖子,缓缓开口道:“陛下...臣没听懂。”
崇祯没有意外。
一个封建王朝的二品大员,肯定无法理解每日工作计划、总结,还有KPI这种东西。
他花了将近十分钟才把这些东西全部讲明白。
邱瑜听懂后震惊不已:“陛下此法无比精妙,实乃考核官员的一大利器!臣以为应当推广。”
“账册上记载了自崇祯十五年到崇祯年十七年元月,陈演任户部尚书时,户部雇佣商号为九边大军运粮草,器械的所有记录。”
“总共有二十八家商号,其中陕西商号有三家,山西商号有十家,浙江商号有五家,山东商号三家,南直隶徽州商号四家,湖广商号三家。”
“据账册记载,每次运送时,其中一些商号会向陈演进献数量不等的银子。多则十数万,少则数千,总数加起来已达数百万之巨。”
“陈演收到银子后并不会独吞,而是将银子分成几份,送给朝中大臣。这些大臣多在吏部,兵部,工部和户部任职。”
“臣顺着这条线索,昨夜已将相关商号的人全部缉拿押在诏狱。并在这些商号里找到了被抢财物,经过连夜审讯,真凶已经招供。”
“真凶是谁?”李邦华忙问道。
“凶手有百余人,分属八家不同的商号。他们知道伪装成抢钱杀人的凶手,实际上是寻找这本账册和这些书信。”
八家商号?
晋党领袖党崇雅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等众人缓过神,李若琏高举手中的书信说道:“这些是陈演与朝中大臣往来的信件,还有陈演私通流贼和建奴的铁证。”
“这些商号就是陈演私通流贼的帮凶,他们想杀人灭证。”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
他们对陈演贪污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前内阁首辅竟然私通流贼和建奴!
贪墨是一回事,私通流贼和建奴是另外一回事。
前者砍头抄家是上限,后者砍头抄家是下限!
“其中一封信是李闯贼手下大将刘宗敏,亲笔写给当朝户部左侍郎沈维炳的,不知为何落到了陈演手中!”李若琏举起一封信,递到李邦华手中。
李邦华脸色难看至极,虽然他知道沈维炳速来贪墨,但给朝廷办事却从来不马虎。
只要户部有钱,前线的军饷和粮饷就不会延误。
这也是他继续重用沈维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万没想到,他竟然私通流贼!
李邦华颤抖着双手打开信纸,里面的内容跃然纸上。
看过之后李邦华咽了口唾沫,“海柯...李指挥使说的可是真事?”
沈维炳虽然非常震惊,但还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否认:“陛下,李阁老,臣冤枉!”
“臣乃大明子民,食君禄解君忧。现在流贼将至,正是用人之际,账册上的内容全是胡编乱造,是流贼的反间计,万万不可相信。”
“求陛下查明真相,还臣清白!”
崇祯面无表情:“诸位怎么看?”
见东林党的沈维炳出事,七八个东林党人纷纷下跪说情。东林党之中属沈维炳官职最高,如果他出了事,东林党将无力与其他党派进行抗衡。
除了这十几个东林党人,其他朝臣站在原地默不作声。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们巴不得东林党人出事,现在不火上浇油已经算是做善事了。
“臣以为此乃反间计也,目的是让我们君臣离心,陛下千万不要上当!”
众人回头,看到说话的人是户部督饷左侍郎党崇雅后纷纷一愣。
党崇雅是晋党,他怎么会帮着东林党说话?
片刻后,众人了然。
账册上有党崇雅的名字,此时帮沈维炳就是帮他自己。
党崇雅是晋党领袖,在他的带领下十几个大臣纷纷下跪,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党崇雅必须谨慎应对。
“范尚书你正好管着工部,朕有一计可使火器发射速度大大提升,名曰纸壳火药。”
“纸壳火药?”范景文不解的问道:“请陛下赐教。”
“将铅丸和火药装进同一个纸筒,装填时将纸筒撕破,把火药,铅丸连同纸筒一起塞进去,既能保证火药装填足够分量,又能增加装药速度。”
范景文拿起一把火铳仔细想了一会,越想越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当时就忍不住开始试验。
他先是找来一张纸,随后从旁边守城士兵身上拿来火药壶和铅丸,然后开始按照崇祯的想法进行包装。
在崇祯的指导下,范景文很快总结出了经验。
弹丸和火药虽然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但二者中间需要隔离,否则气密性会大大降低,影响杀伤力。
其次,包火药的纸不能太硬,太硬无法压实;也不能太软,太软会漏药。
经过几次测试后,范景文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他看着手中的纸壳惊叹连连:“陛下,如果把咱大明军的火药都改成这样,战斗力至少提升一倍!”
“那就立刻安排匠人制作,并配发给守城将士进行测试。”
“遵旨,臣这就安排,只是工部匠人都在制作手雷,短时间内做不了太多。”
崇祯想了想,火铳和鸟铳改用纸壳火药的技术含量较高,火药多了会炸膛,少了威力不足,最好由工部和内廷的兵仗局制作。
至于手雷...技术含量基本没有,只要装药量足够多就行。
“手雷的制作交给内廷,你们工部和兵仗局全力制作纸壳火药。”
“臣领旨。”
针对守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崇祯让内阁督促兵部和户部着手解决。
回到乾清宫已是傍晚时分,王承恩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在殿外等候。
“皇爷,邸报撰写好了。”
“哦?”崇祯对王承恩的办事效率有些刮目相看。
他拿起邸报,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
总体来说写的还行,除了信息有些滞后,标题不够明显外没有别的毛病。
本想安排人连夜印刷,考虑到明天早朝要干的大事,他让王承恩把头版头条的位置空出来,次日再进行印刷。
王承恩刚走,王之心匆匆来到殿门外:“臣王承恩求见陛下。”
“进来吧。”
“陛下,臣已将国公府围了一天一夜,不知陛下有何旨意?”
“行刺朕的凶手确定是朱纯臣?”
“回陛下,证据确凿。虽然没有人证,但物证确凿。”
“那就行,把那些番子都撤回来吧,回来后去兵仗局帮着干活。把朱纯臣和证据移交给刑部,三司会审后再做发落。”
“臣遵旨,臣告退。”
“慢着!”
王之心得到旨意后刚要走,被崇祯喊了回来。
“王之心,你在定国公府收了多少银子?”
“陛下,臣...”王之心刚想说自己没收钱,但看着崇祯犀利的眼神,他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那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睛太可怕了,竟然知道他收了定国公的银子!
“臣...没主动要,是定国公非要塞给臣,臣无奈只好收下。”
说着,王之心跪在地上一脸委屈的磕头。
“呵...看这意思,你是被迫受贿?”
“臣不敢,臣惶恐。”
“朕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收了多少银子,只需要你记住。从今日起,你收的银子九成交给朕,剩下的一成留给自己。”
王之心愣了下,随即跪地不停磕头:“臣不敢,臣生是陛下的奴婢,死是陛下的仆人,臣愿将所有银子都献给陛下。”
小说《大明:距离灭国还有七天?他坐吃等死了》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
这件事一旦被做实,朝堂上晋党的势力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山西商人轻则一蹶不振,重则人死财空。
商号怎么挣钱?
一方面靠朝廷的免税政策,另一方面靠走私。
借着给朝廷运输的机会,将大量走私物品塞进商队之中,遇到检查便亮出朝廷的通关文牒,两个字:免检!
走私的物品有火器,火药,铁矿。
只要运到边关就能获得暴利!
他们一旦在朝中失势,附庸在他们麾下的商号特权也将随之消失。
没有特权就没法走私,更没办法获取暴利!
看着堂下跪着的这些人,崇祯心中渐冷。
党崇雅是晋党领袖!
建奴为什么能发展起来?
朝堂上有晋党,下面有晋商。
晋商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建奴输送军需物资,同时让晋党成员提供朝廷内部情报,诬陷忠臣,排除异己,并借机大捞特捞。
历史上建奴入关后,顺治没忘记给他们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晋商,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
只有八家吗?
非也,这只是贡献最大的八家!
陕西,山西,山东,浙江,徽州,湖广的商人都干过类似的事!
这些人,都得死!
不,死亡对他们来说太仁慈。
抄家,男的千刀万剐,女的全部送入军中。
不过当务之急是擒贼擒王,先把卖国最多的晋党晋商灭了。
晋商有钱,拿到他们的钱朝廷才有免全国田赋的底气。
这些晋商总部虽然不在京师,但京师东边的通州是运河码头。商号为了做生意,大多把银子留在了京师。
至于其他商号,崇祯短期内没有动他们的想法。
朝廷的运输能力无法满z足边关需求,如果把所有商号都灭了,边军会乱!
他淡淡的问:“李阁老,你怎么看?”
众人齐齐看向李邦华。
李邦华拿着信问:“海柯,你真的与此事无关吗?”
“阁老明察,我从未与流贼通过书信。”
“可是这信中附着你写给刘宗敏的信,字迹也是出自你手,你又该作何解释?”
沈维炳后背发凉,他诧异的从李邦华手中拿过书信,仔细辨认起来。
那封信上的字迹确实与他的笔迹十分相似,但细看之下还是能看到些许不同。
他举起信解释道:“诸位请看,这几个字的字迹与我的笔迹虽然相似,但细看之下有三处不同,也就是说,这封信是模仿的。”
有几个熟悉沈维炳的人看过后纷纷点头,细看之下确实有不同的地方。
李若琏悠悠说道:“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三两处不同是沈大人故意为之?好在东窗事发的时候撇清关系?”
“你...”沈维炳指着李若琏想爆粗口,但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这家伙可是锦衣卫指挥使,惹不得。
“其他人怎么看?”崇祯看向其他人。
见东林党和晋党同时出事,其余各党纷纷驻足观看,一言不发。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保持安静,否则极易引火上身。
崇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冷笑着说道:“沈维炳,党崇雅你们先别急着否认,既然锦衣卫找到了账册,无论真假都必须查证。是黑是白,是忠是奸,一查便知。”
“此事关系重大,限锦衣卫两日内破案。”
“陛下,臣冤枉!”沈维炳欲哭无泪,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
以锦衣卫的做事风格,他很可能无法活着出来。
小说《大明:距离灭国还有七天?他坐吃等死了》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
随着崇祯的御驾到来,整个西四牌楼广场瞬间安静下来。
外围的五城兵马司,锦衣卫和东厂厂卫将百姓驱赶到三十五步之外,围城一圈戒备。
空出来的场地一侧摆着一排桌椅。
刑部左侍郎,大理寺卿,左都御史分列而坐,见崇祯到来他们三人起身迎接。
君臣之礼过后,崇祯冷声吩咐:“将人犯押上来。”
随着一声令下,几个厂卫、锦衣卫分别将张缙彦,王正治押到法场中间。又有百余个兵士将张缙彦,王正治的三族百余口人押到旁边。
虽然王之心找到了朱纯臣刺杀皇帝的罪证,但今天崇祯并不想杀他,朝廷的水太深了,让子弹飞一会。
“带张缙彦,王正治!”刑部左侍郎张忻大喊道。
两个锦衣卫推着张缙彦来到监斩台前,张忻问道:“张缙彦,王正治你们可认罪?”
“冤枉!冤枉啊!”
“臣冤枉!陛下让臣认罪,臣没有罪怎么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冤枉啊!”
两人几乎同时喊了出来,声音虽然沙哑,语气却无比坚定。
围观的百姓有些错愕。
皇帝监斩,刑场喊冤,此二人到底是死不认罪还是真有冤情?
张忻嘴角闪过一丝奸笑,他冷哼一声:“你二人罪恶滔天,时至今日还不认罪,冥顽不灵,该死!”
“来人,午时三刻已到,验明正身...!”
他刚要下令处决,围观的人群中有人高呼。
“侍郎大人!他有冤情为什么不让他说出来?朝廷就是这么做事的吗?”
“如果有一天我等被诬陷,是不是有同样的下场?”
“流贼将至,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错杀一个好人!若是错杀,便是自掘坟墓,岂可坐视?”
张忻脸色骤变,他猛地一拍桌子:“大胆,何人喧哗?给本官抓起来。”
周围负责警戒的士兵立刻上前将十几个书生控制住,押到张忻面前。
“汝等是何人竟然扰乱法场,按律该打五十军棍!”
为首的书生脸上虽然带着一丝稚气,但丝毫不惧,他挺着身子喊道:“我等是国子监的贡生,听闻此事后前来围观,见犯人喊冤,便挺身而出!”
“贡生?”张忻皱了皱眉。
贡生皆有功名在身,享有很多特权:见县官不跪,审讯时不受刑,免徭役等。
“生员不得议政,汝等忘了?还不速速离开,否则本官将上报国子监监丞,以正视听。”张忻威胁道。
“侍郎大人难道没听说过,君子可内敛不可懦弱,面不公可起而论之这句话吗?”
张忻怔了下,下意识的看向身后。
百姓们燃起的激情也随着这几句话被浇灭了不少。
他们固然乐意看到官员被杀,但不想看到有人被冤杀,没人敢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受害者。
崇祯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冷笑不止。
这帮官员不敢出面求情,竟然让一帮国子监的学生闹事,简直怂到家了。
他站起身直接无视其他人,对着张缙彦说道:“张缙彦,你有何冤屈?说出来朕听听。”
张忻宛如抓到了救命稻草,他费力的咽下唾沫润喉,声泪俱下的说道:“陛下,昨日朝堂上陛下向文武百官借钱补充军饷,臣只是一时糊涂说错了话,便被安了个欺君之罪,臣...不服!”
“虽然在臣家中搜出几万两银子,但那些都是臣祖上积攒的,还有一些是臣借来周转,借据尚在,何来贪墨一说?”
“好!”崇祯提高音调,他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朕问你,借钱时为何说谎欺君?”
他面无表情的喊道:“刘总兵坠马伤到哪儿了?能不能站出来让我瞧瞧?”
刘泽清的声音再次响起:“刘都督见谅,属下刚敷了药,不能见风。”
“太子殿下就在本官身后,你还不出来施礼?”
见刘泽清不露面,刘文耀搬出了太子。只有亲眼看到刘泽清,才能按照计划行事。
一旦杀的不是刘泽清,后果不堪设想。
这座土城根本无法招架一万五千人的围攻!
刘泽清犹豫片刻后,用极其缓慢的速度从马车里钻出来。他钻出来的同时,附近的亲兵纷纷上前,将盾牌高高举起。
他走下马车踩在柔软的沙土上,拱手施礼:“臣刘泽清参见太子殿下。臣坠马受伤不能受风,只能用盾牌挡着点,望太子殿下见谅。”
朱慈烺转身从刘文耀身后钻了出来,他让太监们高举火把,火焰的红光将他那稚嫩的脸颊映的通红。
“刘泽清,本宫(明太子在官员面前正式的自称)看不清你的脸。”
刘泽清抬头望城头看,确认是太子无疑后,心里悬着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只要太子在,军饷就跑不了。
他吩咐张远:“拿火把来,让皇太子殿下看清楚些。”
沾了油的火把刚拿过来,不等张远高高举起。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大地为之颤抖,烟雾和灰尘腾空而起,碎石铅丸四散开来。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先是一团浓烈的烟雾喷涌而出,紧接着巨大的冲击力和爆炸的碎片飞一样的向四周射去。
离爆炸点近的士兵和战马首当其冲,运气好的士兵只受到了声波攻击。
他们纷纷捂着脑袋和耳朵,身体不受控制的从战马上跌落。战马在巨大的声响下受惊嘶鸣,挣扎着逃向远方。
运气不好的直接被碎石和铅丸射中,有的鲜血直流惨叫不止,有的血肉模糊直接丢了性命。
痛苦的哀嚎声,战马的嘶叫声,求救声,询问声,喊声,哭声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让场面十分混乱。
离爆炸点远的也受到了波及,好在这些士兵和战马早已习惯了炮火声,稍微调整后就恢复了队列。
“妈的妈我的姥姥,怎...怎么回事?”一个士兵捂着半聋的耳朵,看着远处的浓烟艰难的咽着唾沫。
“不...不知道,好像是总兵大人的马车炸了!”
“总兵,总兵大人没事吧?”
“应该没逝...走,去看看!”
铁门关外的士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猜测是城内开炮,也有人认为是天降异象。但无论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想看看总兵大人的情况。
近五千骑兵一边警戒,一边朝发生爆炸的地方聚拢。
城墙上。
刘文耀站起身,将压在身下的太子拽起来,“太子殿下,您没事吧?”
朱慈烺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表示没事。他急不可耐的走向城墙,扒着上面的垛口往下看。
爆炸产生的烟雾和灰尘已经散去,现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深坑直径有一丈,深度也将近一丈。焦土、碎石以及各种残骸散落一地。
“刘都督,找到刘泽清了吗?”朱慈烺问。
刘文耀借着月光使劲看了又看,最后指着深坑远处的一具残骸说道:“应该是死了!”
朱慈烺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半个身子倚在垛口旁,声音疲惫:“那就好,那就......”
不等朱慈烺把话说完,城外突发状况。
崇祯眉毛皱了皱,三句话可谓滴水不漏,他终于领略到内阁首辅的厉害。
与此同时,也动了杀心!
作为穿越者,他何尝不知魏藻德的心思?
崇祯点点头,示意所有人回归本位。
他看着众人,目光渐冷:“众卿刚才所言,朕都听到了。有些人说的话是有理有据,有些人则是一派胡言!”
“光时亨,你说京师守得住,怎么守?说来听听!”
光时亨眼珠一转,说道:“京师有百万之众,召集十万百姓肯定能守住城池。”
崇祯阴沉着脸问:“如何召集?抓壮丁还是募兵?抓壮丁就不怕他们临阵倒戈吗?募兵钱从何来?军饷可以拖欠,粮饷呢?难道让百姓带着干粮守城?”
在崇祯皇帝一连串的问号攻击下,光时亨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他结结巴巴的说道:“这...钱粮是户部的事,臣只说策略。”
崇祯大怒:“好,朕现在就提拔你为户部尚书,你若是没有对策,朕就砍你的头。”
崇祯并非真正发怒,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完全勾不起他的怒火。
他这么做是为了引魏藻德出手。
光时亨是小卒,他身后的魏藻德才是大BOSS。
光时亨吓得连忙跪倒在地:“陛下息怒,臣...臣也是为了朝廷。”
崇祯冷冷一笑:“光时亨你是聋子吗?朕已经封你为户部尚书,请说出你的对策!”
听到那个请字后,光时亨真的害怕了。大明朝没有几个活人能承受起崇祯的请字,有也不是他。
他跪在地上以头撞地:“陛下恕罪,臣不该在朝堂上胡言乱语,请陛下息怒!”
崇祯看着跪地求饶的给事中光时亨,心中仅存的一点怜悯也消失不见。
如果光时亨死不认罪,崇祯会因为他硬骨头而放过他。
毕竟大明末年的文臣早已没了风骨,好不容易出来一个,不能灭种。
可是,他的骨头也是软的。
崇祯摆手让光时亨退回本位,现在时机不到,一会再杀也不迟。
他扫视众臣,悠悠说道:“朕非昏君,自天启七年八月继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本欲中兴大明,奈何天不遂人愿。今流贼猖獗,建奴放肆,人心不稳,京师难守!”
“朕,很失望。不止对自己,对你们也很失望。”
“臣等该死,上不能与君分忧,下不能解百姓离苦。”内阁首辅魏藻德跪倒请罪。
事可以不做,但样子该做还是得做。
“臣等有罪!”众臣跪倒一片。
“都平身吧。就依李邦华之计,太子,永王,定王,六宫内眷以及内臣百官等少数人随行,其余人等与朕固守京师,等待勤王之师。至于去往南京的官员名单,就由李邦华来拟定吧。”
崇祯早就想明白了,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摆在他面前有且只有三条路。
守,逃,谈!
首先排除逃。
一旦南逃,后果不堪设想。
天子守国门的承诺变为一纸空谈;辽东几十年,无数男儿血染疆场,成为一场游戏。
更重要的是,千里勤王的吴三桂会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如果他像历史上那样投降建奴,历史的悲剧可能会重演。
届时崇祯不但对不起朱家先祖,对不起战死沙场的英灵,更对不起涂炭的生灵。
其次排除和谈。
有明一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他不能坏了底线。
最终答案:守。
历史上崇祯耗时十七年都无法拯救大明,一周时间他更做不了什么。
当下唯一能做的是守住北京。
只要李自成攻不进北京,大明的基本盘就还在,历史或许可以重新书写。
“陛下圣明,臣等谨遵圣旨!”李邦华带领三十多个官员下跪领旨。
支持李明睿的官员们见状,经过短暂的思考后,也纷纷跪地领旨。
皇帝把随太子出行的大臣名单交由李邦华拟定,说明什么?
说明李邦华已经在悄无声息间受到了重用。
想去应天避难,必须向李邦华站队。
眨眼间,朝堂半数官员跪地接旨。
魏藻德脸色凝重。
对他来说,上策是把皇帝皇子全都留下献给李自成。
只要逼迫崇祯下了退位诏书,就是天大的功劳,李自成也会给他升官加爵。
但若是让太子跑了崇祯留下死守北京,事情就复杂了。到时候不但没有功劳,反而会被特殊针对。
他早就听说,大顺对待没功劳的明朝官员非常残忍。
投名状没了,他心里没底。
政治游戏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皇帝和大部分官员都同意太子南迁。
这件事已经无法逆转了。
只是他想不明白,换做平时崇祯肯定会犹豫不决,要么召内阁后殿商议,要么回宫后左思右想。
今个儿这是怎么了?竟然在朝堂上做了决定!
“陛下!”魏藻德试图唤醒曾经那个犹豫不决的崇祯。
“朕意已决!”崇祯一口回绝魏藻德,继续说道:“去往南京的官员务必认真辅佐太子,留在京师的全力协助朕,一起抗击流贼!”
“是!”四十多个官员同时回应。
“现在说第二件事。”崇祯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刚才朕让人算了算,京营守军的饷银,加上募兵的钱,有一百五十万两银子的缺口。”
“现国库空虚,无钱可用。都说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为了抗击流贼,众卿想想办法!只要凑得百万白银,就能守住京师!”
文武百官非常默契的同时低下头。
关于银子的话题从崇祯元年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国库每年收的钱入不敷出,如果没有万历一朝攒的内帑钱,军饷早就不够了。
皇上让他们凑钱,怎么凑?去哪凑?
如果能凑到钱,大明朝也不至于被一伙流贼搅得天翻地覆。
见众人不说话,崇祯假笑道:“既然众卿没有办法,朕倒是有个主意!”
“请万岁明示!”内阁首辅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第一时间和皇帝打起了配合。
“捐钱!”
在场的文武官员继续沉默,老套路了,自崇祯十六年起捐了不知多少次。
“众卿有没有捐银子的?捐银者升官加爵!”崇祯表面上着急,内心是另一种想法:众卿,朕给你们机会了,你们把握不住可别怪朕!
李邦华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清楚,崇祯要动手了。
“臣李邦华,万历三十一年入仕为官,家里的一分一毫都来自朝廷,现朝廷有难,臣愿将家产悉数奉上,以助剿贼。”
“好!李邦华忠心可鉴,朕大大有赏!”崇祯拍案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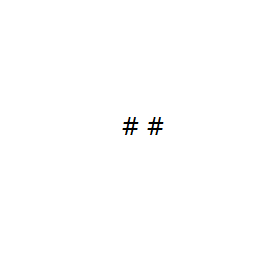
最新评论